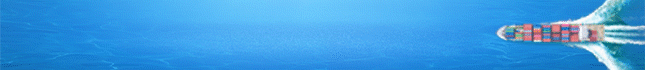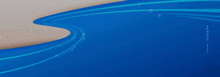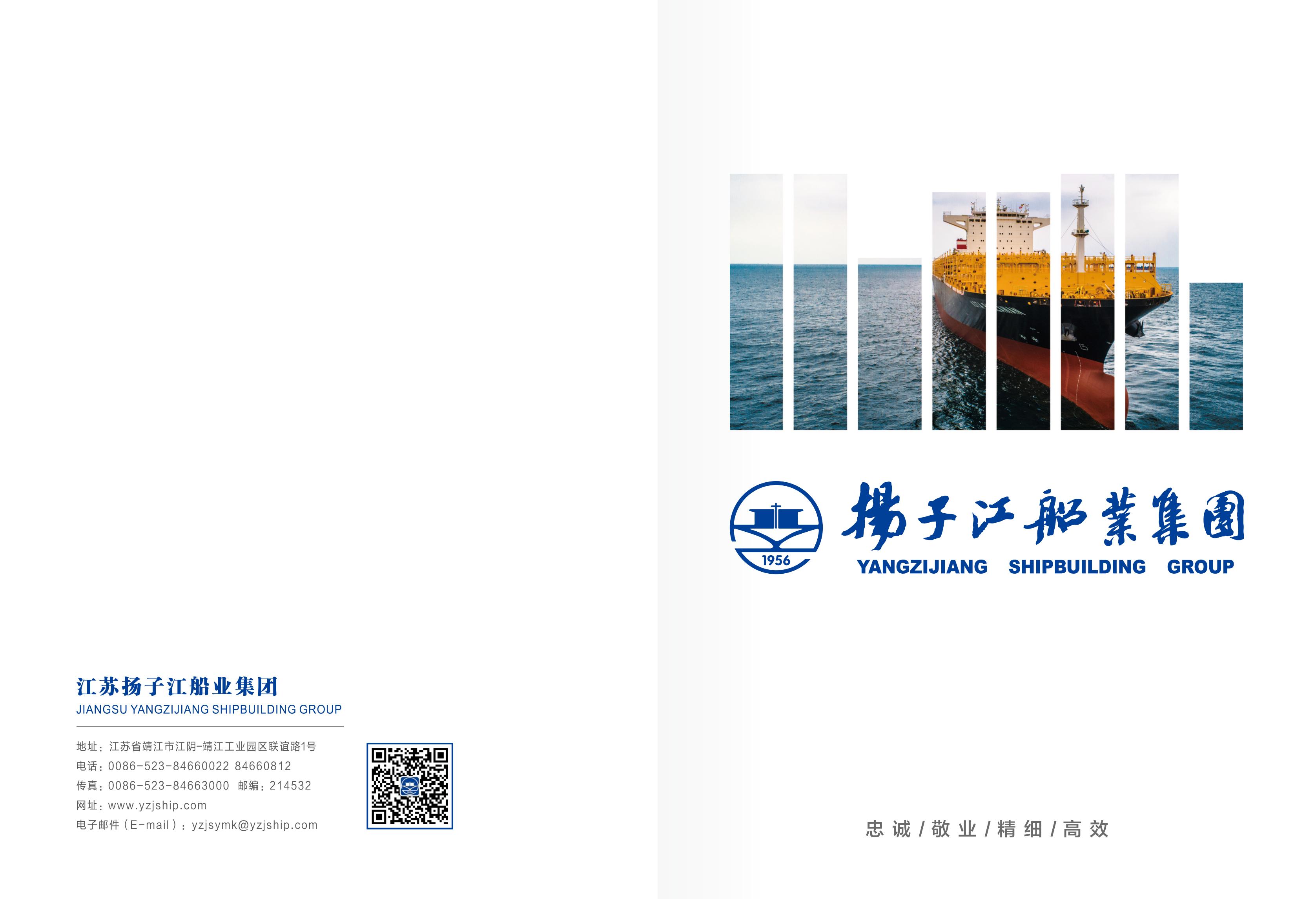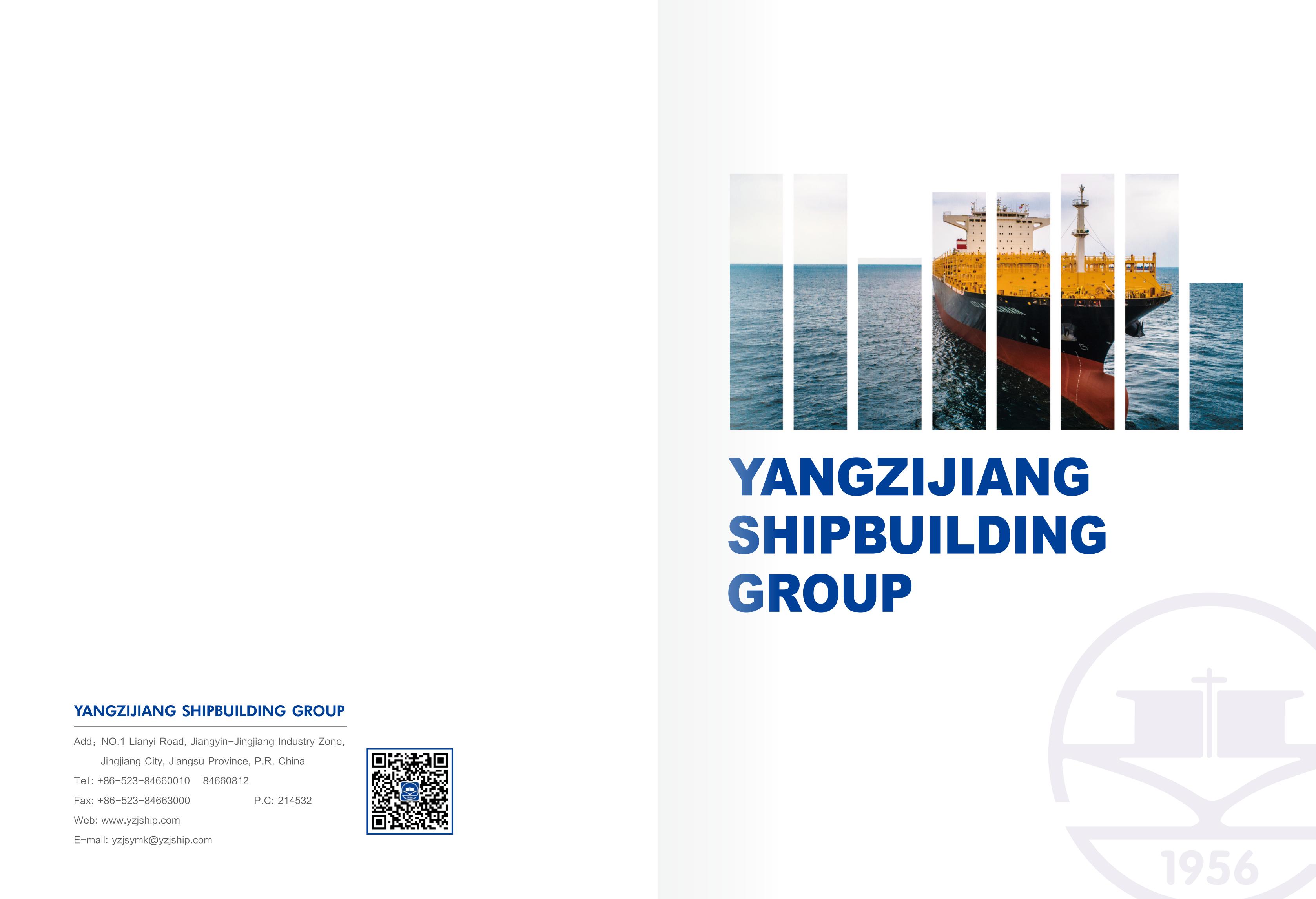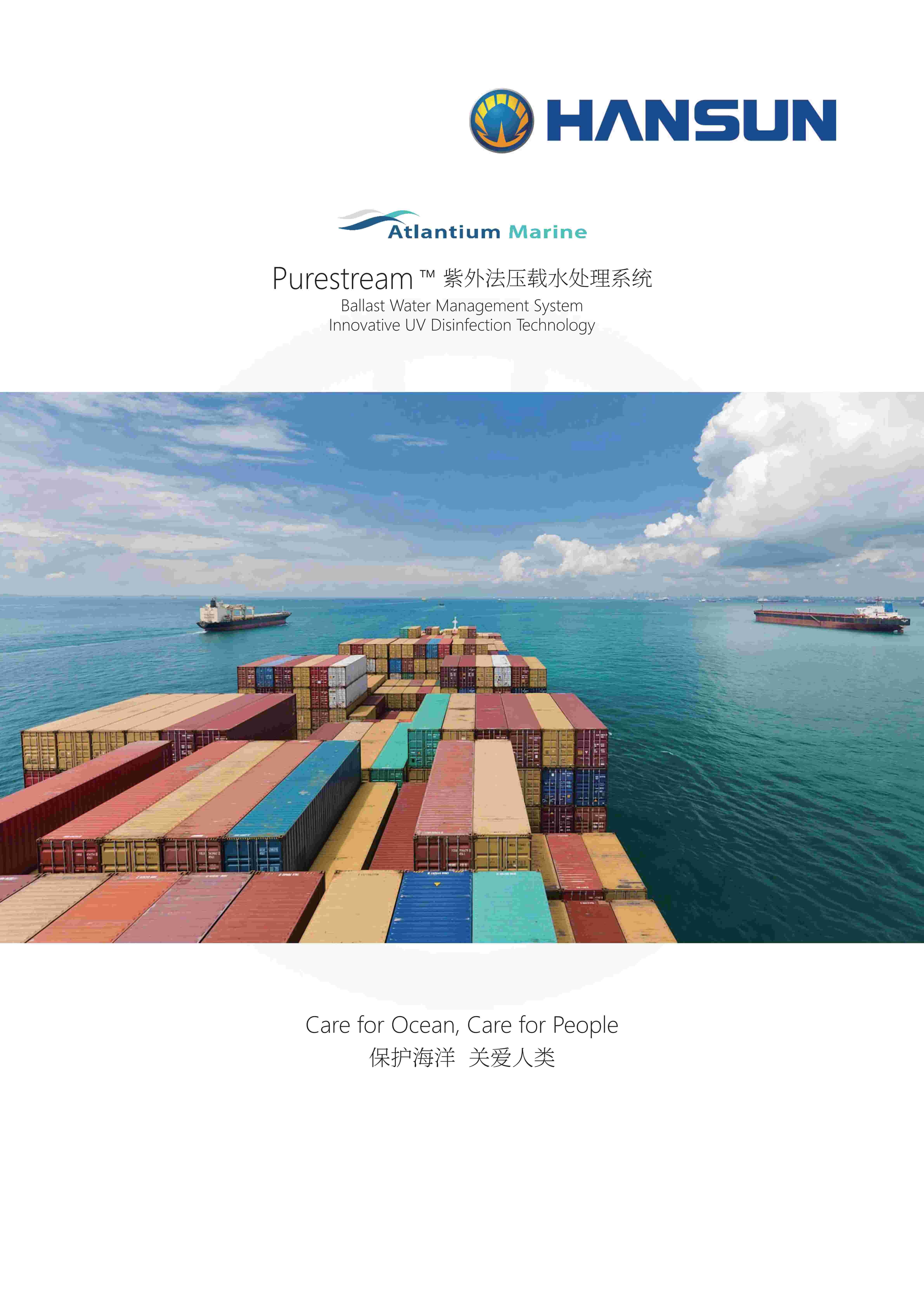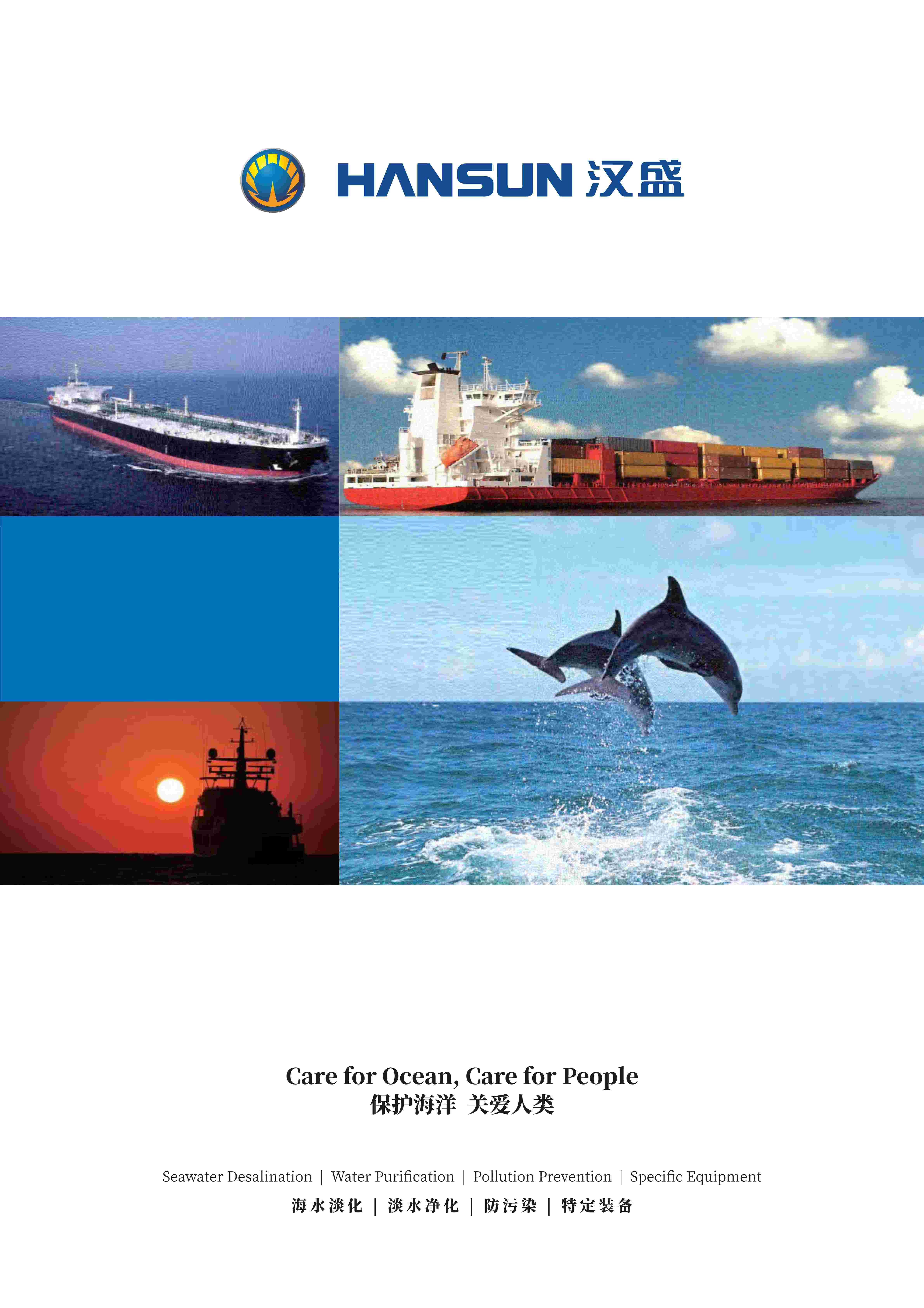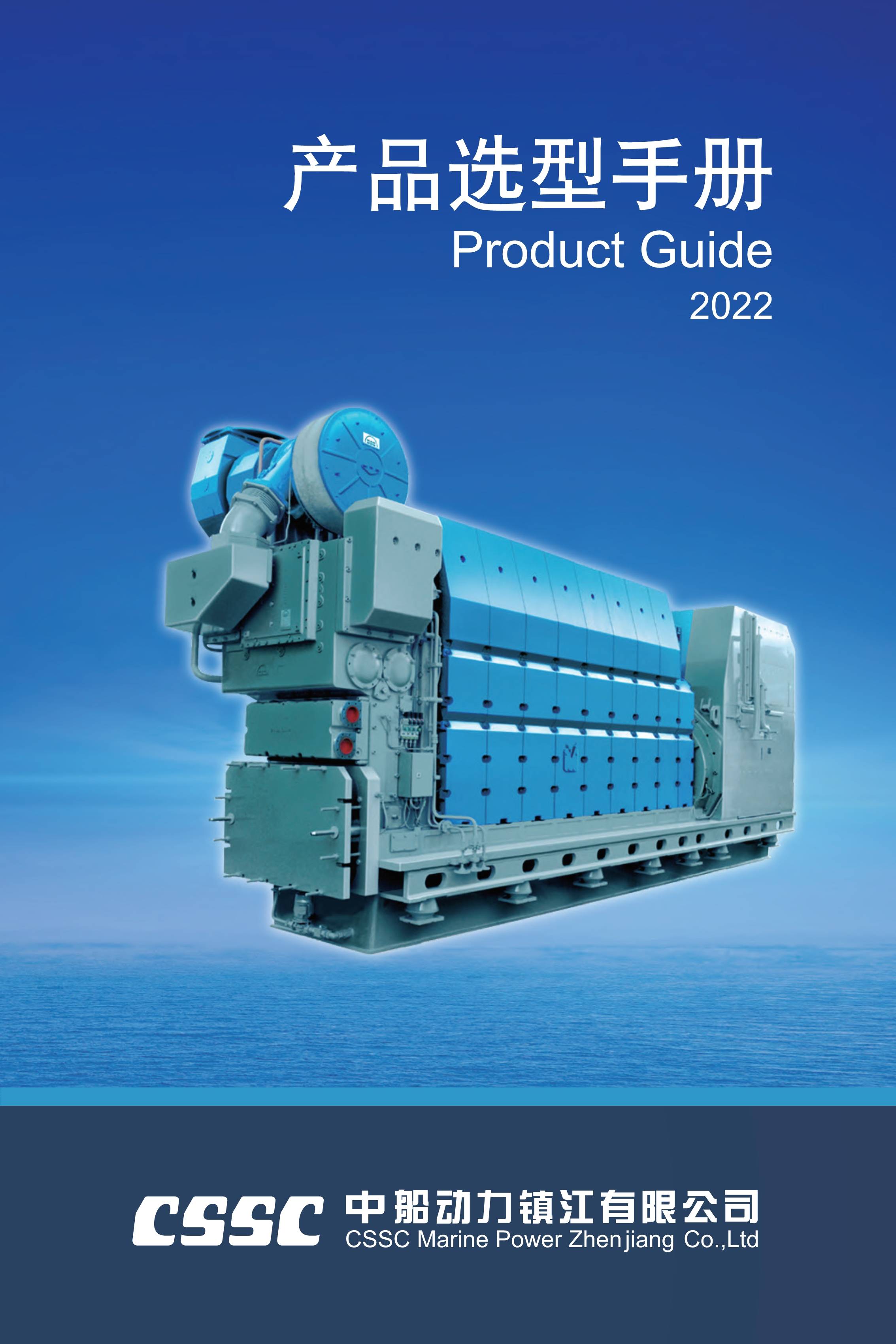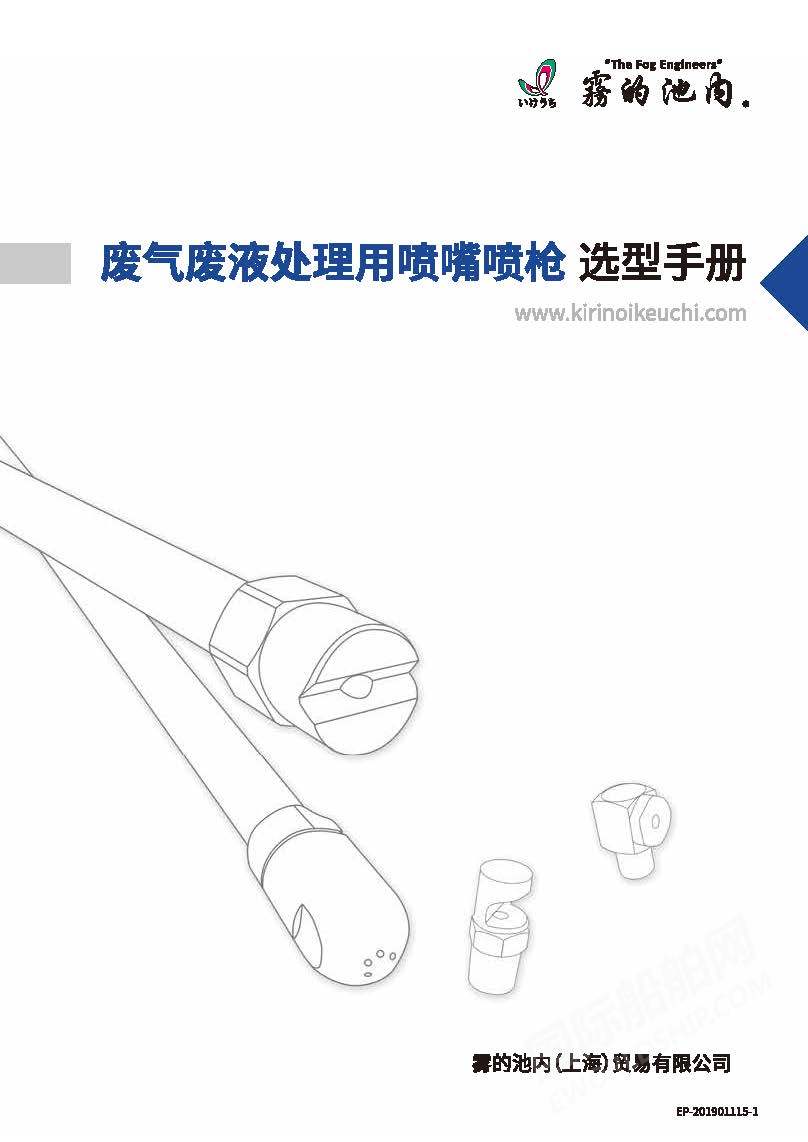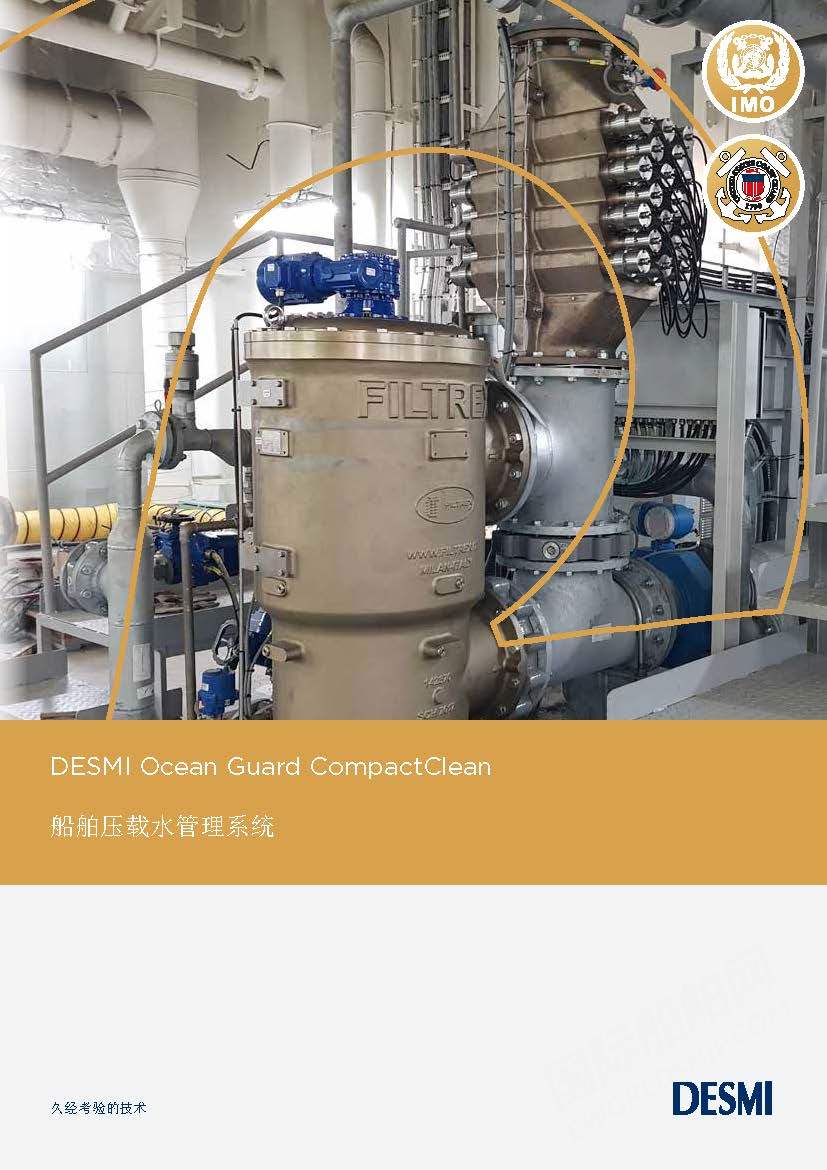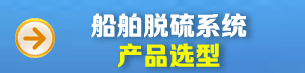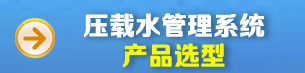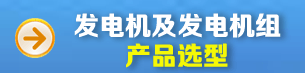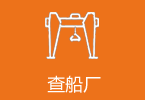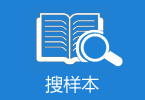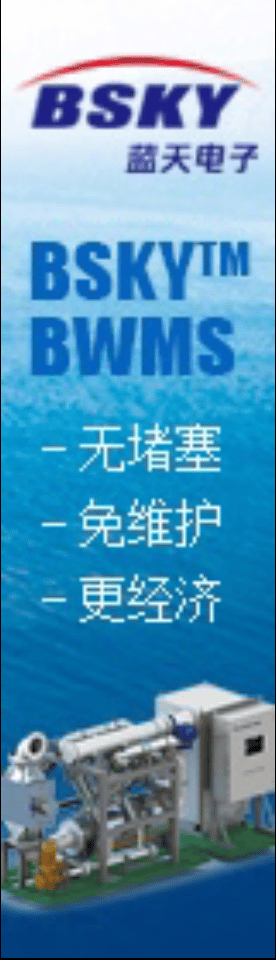國際船東一怒扣下中國遠洋的輪船,是正常的商業博弈?還是拿商業誠信作為談判的籌碼?中國遠洋幼稚豪賭FFA背后,中國企業進入國際金融衍生品領域的脆弱再次暴露——危險的FFA游戲慎入。
2008年,中國遠洋簽下租約的輪船日租金由簽約價的8萬美元降到了現在的2萬美元。高額租金意味著中國遠洋做一筆干散貨生意就虧一筆。記者調查發現,曾經在FFA游戲中豪賭的中國遠洋,只是這場游戲中的菜鳥,興奮之余連基本常識都忘了。
類似中國遠洋這樣的投資失敗案例近幾年層出不窮。對于中國企業來說,金融衍生產品投資游戲似乎是高危性的,但同時高額回報又誘惑著它們。
“老賴”中遠
中國遠洋8月底發布的2011年半年度報告顯示,該公司總資產達1563億元人民幣。但就是這家千億級的大型企業,卻在近期屢次被國際船東爆出拖欠其租船租金,變成了“老賴”。
希臘“船王”喬治·伊科諾莫這一次成為中國遠洋賴租金的大戶,旗下Dropships、Classic Maritime、Cardiff Marine三家公司跟中國遠洋劍拔弩張,向相關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扣押中國遠洋輪船。同期,希臘Navios、香港金輝航運等公司也加入到希臘船王的陣營,與中國遠洋對抗。
中國遠洋是全球最大的干散貨船隊運營商。截至2011年6月30日,中國遠洋經營干散貨船舶435艘,其中擁有船舶234艘,租入船舶201艘。
伊科諾莫公開宣稱,中國遠洋拖欠的租金估計已高達2500萬美元,他旗下公司有總計5億美元的租賃款可能受到中國遠洋拒付行為的影響。世界航運界指責中國遠洋毫無契約精神,甚至質疑中國遠洋的現金流已出現問題。面對壓力,中國遠洋陸續向伊科諾莫、金輝航運等船東支付租金。
為什么有支付能力的中國遠洋此前要拖欠船東租金呢?這就得提到這些租金的性質——FFA。
FFA是買賣雙方達成的一種遠期運費協議,協議規定了具體的航線、價格、數量等,且雙方約定在未來某一時點,收取或支付依據波羅的海航交所的官方運費指數價格與合同約定價格的運費差額。
“FFA就像期貨一樣。”中國國際海運網總裁康樹春向記者介紹,“國際干散貨航運市場變動較大,有時一周的變動就能高達20%,這種變化給航運企業把握市場、穩健操作帶來很大難度,FFA可為航企規避市場波動風險發揮重要作用。此次發生拒付糾紛的基本上都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尚未爆發時簽署租賃協議的船只。”
康樹春介紹,2008年上半年,大宗商品市場繁榮,國際航運市場處于“膨脹期”,運費也很高。當時反映干散貨運價的波羅的海指數(BDI)一度沖到高位11793點。但金融危機的到來,使得海運市場一瀉千里,BDI指數一度跌至663點。兩年來,BDI指數有所反彈,但仍低迷,2011年9月5日BDI指數只有1750點。
中國遠洋與國際船東簽署的這批租賃協議,租約為3-5年。當時租賃一艘巴拿馬型船的價格超過8萬美元/天,但如今,這種船型的日租金還不到2萬美元。過高的租金,也直接反應在中國遠洋的業績上。
中國遠洋2011年上半年虧損27.11億元人民幣。在干散貨業務上,營業成本上漲2.7%,但營業收入大幅下滑27%;利潤率為-7.5%,營業利潤同比下滑-31.1%。這意味著中國遠洋每做一筆干散貨運輸的業務,就虧損一筆。而這很大因素來自于此前約定的偏高的運費。
在其2011年中報中,中國遠洋稱,所屬干散貨船公司持有的FFA期內發生凈損失金額為733.16萬元人民幣,而2010年同期凈收益金額為3669.10萬元人民幣。
稚嫩“菜鳥”
面對2008年簽下的天價FFA,中國遠洋選擇與船東洽談,爭取能降低租金。喬治·伊科諾莫透露,在6月份時收到了中國遠洋希望談判以降低租金的請求,但被其拒絕。遭其拒絕的中國遠洋,采取了拒付租金這種極端方式進行對抗,作為談判條件。只不過,他們沒有等來船東們的理解,而是法院的傳票。
中國遠洋面對船東拒絕聲稱,下屬干散貨運輸企業的所有行為都應被認為是中國遠洋正常經營中采取的市場行為,符合投資者的基本利益。作為一家上市企業,為股東爭取最大回報一直是首要考慮的,調整租金是基于降低成本,反映了股東的訴求。此舉為在干散貨運輸市場不景氣之際的正常的、基于市場所作出的行為。此外中國遠洋還督促業界共同克服現有的問題并信任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
對此,喬治·伊科諾莫認為,中國遠洋缺乏處理長期國際租船合同的經驗,未能在合同中對沖租金變化風險,中國遠洋2008年和其旗下公司Dryships簽署的船舶租賃合同中“沒有對沖風險的條款”。中國企業缺乏國際市場和現貨市場的從業經驗,目前他們仍在學習的過程中。
荷蘭海事信息咨詢公司Dynamar BV的分析師德克·維瑟則表示,如果承運人簽訂的包租合同令承運人得到的貨運收入少于包租成本,那么有關各方重新訂立合同的做法并不鮮見。現在,BDI大幅跳水,證明重新商議合同顯然是有根據的。航運經紀商BRS就公開表示,曾在金融危機后成功協調租賃雙方重新商議合約價格。
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涉外法律服務專業合伙人喬文豹也認為,在市場出現劇烈變動時,合同雙方可以坐下來談,這是有先例的。在很多領域,合同雙方在市場出現急劇變化時都可談判更改合同。但這一次船東們如此強硬,只能說在特殊時期全球航運市場的日子都不好過,資金都很緊張。
康樹春也表示,業內普遍規律是,航運企業的盈虧成本線至少在2500點以上,可以說各大公司均在虧損線掙扎。全球散貨船東將面臨至少一年現金流量疲弱的情況。加上經濟前景疲弱,干散貨運輸市場將繼續疲軟,預計散貨運輸市場在2013-2014年前不會出現實質性的反彈,所以這些企業不惜冒著失去大客戶的危險,主要是想先過了目前這一關再說。
喬文豹建議,中國遠洋可以嘗試利用“情勢變更”要求船東降低運費。“情勢變更”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履行完畢之前,如果出現某種不可歸責于當事人原因的客觀變化,若仍然履行合同會給一方當事人造成顯失公平的結果,法律允許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而免除違約責任的承擔。“情勢”指作為合同法律行為基礎或環境的一切客觀事實,包括政治、經濟、法律及商業上的種種客觀狀況,如國家政策、行政措施、現行法律規定、物價等。
不過,喬文豹強調,FFA本身就是高風險高回報的具有金融期貨性質的合約,而運費下降如果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法院就難以支持了。
德衡律師集團事務所律師王海軍則認為,若合同雙方沒有寫入“情勢變更”一項,也沒有“對沖風險”的條款,中國遠洋就很難打贏這場官司。他認為,中國遠洋自身對市場的判斷力不足,中國遠洋拒付的事實很明確。但他表示,雙方仍可以談判。“為了雙方的長期合作,可以各自讓步,中國遠洋的市場地位能為其增加談判條件。”
喬文豹介紹,在國際貿易領域,合同雙方會在合同中附加條款,如在匯率、原材料等方面有所約定,比如當匯率或者原材料等出現較大浮動,一般為10%時,合同雙方可以重新商議合同價格。
據悉,中國遠洋將赴歐洲與船東談判。而且有部分船東也正在與中國遠洋就FFA進行重新商議。
豪賭代價
中國遠洋為何沒有在合同里加入“對沖風險”這一條款呢?
中國遠洋投資者關系部相關人士表示對此事不了解,中國遠洋運輸(集團)運輸部副總經理張建輝也表示對合約等事情并不了解。記者從《光船租賃合同(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制定)》范本以及多份航運租船合約中并未發現當中有“對沖風險”條款。
中外運物流部相關人士介紹,她所接觸的租船合約中,從來沒有對“對沖風險”機制有所設定。不過她強調,中外運租船合約很少有一年以上的長期合約,所以風險相對較小,“只有像中國遠洋這樣的大公司才敢簽如此長的時間,才敢如此豪賭。敢于如此豪賭也是因它曾嘗到過甜頭。”
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國際航運市場租金不斷上漲,但手中持有的FFA,給中國遠洋帶來了巨大收益,中國遠洋2008年第三季度季報顯示,中國遠洋當年FFA已交割部分共實現收益18.74億元人民幣。
但形勢急轉直下。2008年12月16日,中遠對外發布公告稱,截至2008年12月12日,公司干散貨船公司持有的FFA協議公允價值變動損失合計為53.8億元,扣除已交割部分實現的收益14.3億元,中遠持有的FFA協議當年浮虧39.5億元。中國遠洋第三季度凈利潤人民幣55.6億元,這也意味著當前FFA公允價值變動的損失規模幾乎相當于該公司第三季度的收益。
根據中國遠洋2011年半年報,該公司未來第一年,已簽訂的正在或準備履行的租賃合同中,待付租金高達161.84億元人民幣;未來第二年為123.91億元人民幣;未來第三年91.33億元人民幣;未來第四年及以后為615.75億元人民幣;合計992.83億元人民幣。這著實不是一筆小數目。
波羅的海交易所主席曾說,“運費已經真正成為一種可供交易的商品。”FFA交易給航運市場提供了一個對沖風險的管理工具,然而,潛在的高額利潤使它越來越像一個對賭的游戲,尤其是隨著國際投行的逐步滲透。
由于在BDI指數持續下跌、運費反彈無力的背景下,中國遠洋沒有辦法對過去一年里海岬型船租金暴跌進行套保,損失慘重;同時,與租船市場上的其他一些參與者不同,中國遠洋也沒有把租來的船用來投機,只是做預定貨盤,所以波動的租金成為中國遠洋一個潛在的危機點。
“FFA是高風險高回報的合約,‘對沖風險’的介入,將大大降低合約的風險性,但同時也將降低其回報率。基于此,我認為中國遠洋并非不知要加入‘對沖風險’此項,很可能是出于對當時市場的樂觀判斷,對協議的自信。”喬文豹表示,“FFA市場有其自身的特點,要求參加者必須熟悉相關的游戲規則,且還要具備專業的海運操作素質。”
喬治·伊科諾莫透露,中國遠洋當初與旗下公司簽訂的FAA都是固定租金合同,存有投機心理。
屢交學費
中國遠洋FFA之殤,讓市場馬上想到了2009年中國航空及航運公司的遭遇。當年,中國一些國有航空和航運公司因為簽訂用于對沖石油價格上漲的衍生品合約蒙受巨額虧損。另外,中信泰富受困外匯累計期權、深南電A對賭原油價格等也損失慘重。
金融衍生產品最根本的作用在于為企業提供了套期保值的手段。但現實情況卻是中國企業非但沒有利用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實現應有的套期保值目的,反而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高位回落時深陷巨額虧損的泥沼。
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李偉曾發表文章披露,截至2008年10月底,68家央企涉足金融衍生產品業務浮虧114億元人民幣。喬治·伊科諾莫用一句話對央企的投資進行了總結:中國企業缺乏國際市場和現貨市場的從業經驗,目前他們仍在學習的過程中。要獲得經驗就要付出代價。
國內專家們也分析這與中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發展滯后、缺乏該方面人才有關。為多家中國企業代理過跨國業務的北京市維詩律師事務所執行合伙人楊安進則從管理等方面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出現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企業已處于適用市場規則的全球市場經濟中,必須尊重市場規則、法治原則;但另一方面,一些中國企業決策者長期習慣于寄生于權力下的非市場規則,不習慣于尊重市場、契約、法律,且缺乏相應的對決策者的追責機制,導致這些決策者用國內的一套做法去做海外的生意。
在楊安進接觸的許多存在糾紛的重大海外合同中,由于中國公司對海外的商業模式、業務環境、法律環境等方面缺乏充分的調研,不懂游戲規則,以一種無知者無畏的狀態就做出了某個重大商業決策。
“避免風險的最后一道關口就是合同的法律審查。但在我代理的訴訟中發現,有些中國公司,尤其一些國有企業,因為各種內部原因,在此類合同審查時操作比較粗糙。有些公司并沒有非常重視合同的法律審查,也許就在某次商務談判的酒后一時興起而簽約,將法律風險、商業風險置之腦后。”楊安進強調。
此外,一旦此類合同在履行中出現問題后,當事人應當本著尊重約定、尊重法律的原則,合法地處理自己面臨的問題,以最小限度避免損失。但有的企業在此情況下往往急于推卸責任,試圖將簽約時犯下的錯誤進行掩蓋,錯上加錯。許多企業在此情況下不僅最終要承擔違約責任,還背上了無知、缺乏誠信等印記,導致其市場信用大為下降,甚至嚴重影響了中國企業和國家的形象。